性侵 案件起訴率只有3成?!制度要友善,報案才有力量!
撰文/許靖健(研究發展處 倡議專員)、蕭淳方(公民對話處 媒體專員)
編輯/蕭淳方 (公民對話處 媒體組 專員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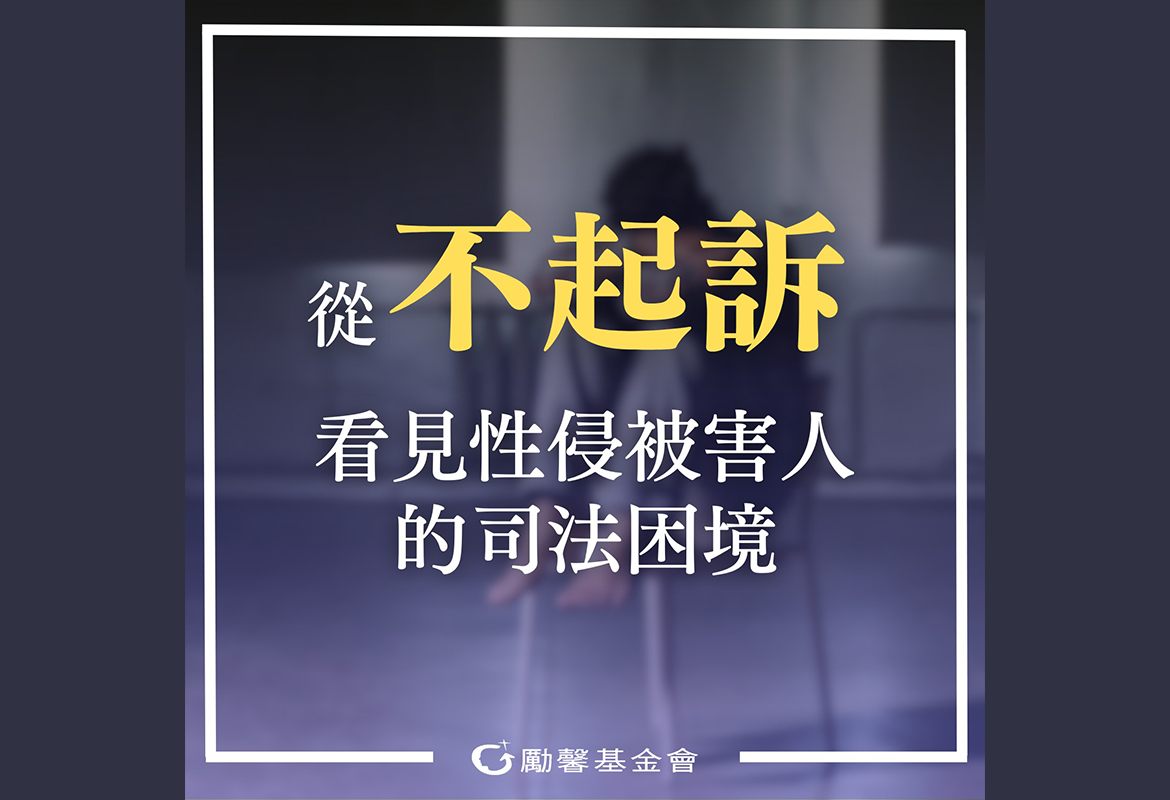
2024年,法務部統計性侵案件終結為5,776件,起訴為1,923件,起訴率僅有33.3%。
這些數字可以看見,司法體系對性侵案件的處理仍有改善空間,我們需要更友善、有效的制度,才能讓報案成為找回正義的開端,並為被害人提供應得的支持與回應。
從統計數據與勵馨的實務觀察來看,即使被害人選擇報案並進入司法體系,在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困難,這些困境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:
證據困境與「完美被害人」迷思
刑事訴訟採嚴格的證據法則,要求有「積極證據」才能啟動或支持訴訟。
然而多數性侵發生於密閉空間,沒有第三人在場,缺乏明確人證或物證。被害人若在受侵害時未能即時驗傷、保留證據,或馬上求助,案件很容易被以「證據不足」為由不起訴。
此外,司法體系與社會普遍存在「完美被害人」的僵化想像:認為被害人應該拼命反抗、馬上報警、身心俱傷,甚至表現出 PTSD 等強烈反應。如果表現得冷靜、理性,或記憶有斷裂,便容易被懷疑「說謊」、「誇大其詞」,更可能被認為「根本沒被性侵害」,甚至遭加害人反控誣告。
司法不友善 帶來二次創傷
司法程序冗長繁複,被害人需要面對長時間的調查和審訊,這對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壓力。
性侵被害人常因創傷反應而出現記憶斷裂、敘述反覆的現象,卻常在司法攻防時被認為「證詞前後不一」,進而導致不利局面。
如果司法人員缺乏性別敏感度與創傷知情概念,被害人的處境可能被誤解,或因「表達不清」而被質疑,不只造成二度傷害更可能錯失司法保護。若警察、檢察官或法官對性侵案件缺乏知能訓練,案件可能在偵查與審理階段遭遇誤判、推延,甚至草率結案。
社會氛圍與報案壓力
社會氛圍對性侵被害人的影響同樣深遠。
受「性別刻板印象」與社會長期的「性侵迷思」影響,許多被害人選擇隱忍不報。一旦報案或求助,便要面對「為什麼不拒絕、逃跑」、「是你穿著暴露」或「是否挾怨報復」等苛刻質問。
這些迷思常常在警查詢問和法庭上反覆出現,使得被害人再次遭受羞辱和自責,形成典型的「二次傷害」,讓人挫敗、不知所措更無力應對。
讓司法真正成為支持被害人的後盾
性侵被害人往往期待透過法律找回正義,儘管通報案件數逐年上升,但面對起訴的高門檻,讓大量案件無法進入司法程序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被害人心中湧現的不僅是對制度的質疑,更是求助未被聽見的深深失落和無助。
要改善這一情況,除了持續強化執法人員的性別意識與創傷知情概念外,勵馨更要呼籲建立性侵害的證據法則、心理衡鑑交由專家證人判讀等制度改善,讓被害人在更友善的司法環境中獲得支持。
同時,整體社會也應積極打破性侵迷思,停止對被害人的指責,並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。唯有如此,性侵被害人才能在體制中真正被看見、被理解、被保護。
已發送 Email 驗證信給你,請點擊信件連結以完成訂閱程序
暫時無法接受訂閱,請稍候重新嘗試